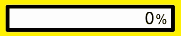
记者:王梓辉
实习记者:成佳阳、曾笑盈
因为媒体的报道,“远程直播授课”这种教学模式突然变成了一个大众热议的话题,其实它已经在中国很多地区存在了很久。
根据教育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创始人刘泓的说法,“早在本世纪的头几年,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学校的远端直播班就开始使用了。”随后,一些地区范围内的名校也相继开始建立自己的远程直播授课体系,除了报道中已经做了16年的成都七中外,湖南的长郡中学等名校也都在2005年左右开始了相关的尝试。

2015年9月8日,河南省新乡市,辉县高庄乡金章小学五年级的19名学生在教师新安装的投影屏幕前,体验了由北京五名优秀教师教授的直播课程。(图 | 视觉中国)
智能学习服务公司洋葱数学的创始人杨临风一直关注教育领域,他告诉本刊,依靠真人老师1对1或1对多的直播授课,是在线教育2.0时代探索出的商业化变现手段。而成都七中采用的网络名师直播+本地教师辅助的“双师课堂”,便是此阶段下为了扩大服务人群规模的时代产物。
引进这些直播课的学校大都来自教育资源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生,大家对远程直播课的评价和认知并不相近。一块屏幕背后的争议,其实体现了教育这个永恒话题的复杂性。
毕业于湖南邵东县邵东七中的尹飞在2005年就参与了直播课,他告诉本刊,当时是因为长郡中学的直播班在做推广,他们学校也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教学水平,第一次尝试了远程直播课。几年之后,等到他弟弟在2011年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把直播课变成了录播课。“原因可能是直播课导致本校老师没有很大存在感。另外,有的同学跟不上。”
与此前报道中云南禄劝第一中学令人兴奋的情况稍有不同,邵东七中的直播课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他们放弃了直播的形式。尹飞自己总结了三个主要问题:
1.直播班老师与远程学校老师在教学水平、知识层面的差距很大,导致后面就算远程学校本校的老师上课,本校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也不太愿意听;
2.长郡学生的基础都比较好,老师上课讲题速度都比较快,导致远程学校成绩较差的学生跟不上课程,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3.因为直播班同时跟几十所中学同时进行,所以课堂互动很少。
从其他不同学校受访同学的反馈来看,这三点基本能概括远程直播课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大凉山地区的西昌一中也接入了成都七中的直播课,一位毕业于该校的同学也向我们抱怨称,“我们听课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师讲得很模糊,上课有种‘囫囵吞枣’的感觉。可能成都七中的老师说一句话,他们的学生就能想到十句;到了我们那,我们只听懂了半句。”而且因为试点班级是强制性的,不适应这种教育方式的同学也没得选。
但尹飞也发现,他们那一届的升学率确实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考上二本的人数从之前的10-20人变为了50-60个。这种提升是否能完全归功于远程直播课无法定论,但尹飞也承认直播课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帮助。
“网班课的老师押题一定要听。”尹飞说道,“长郡的老师压中了高考理科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这可能这是他们精心备课的结果吧。”另外,视野上的差距是所有人都体会到的,“长郡同学写的作文比我所有买到的所有作文书都好,可能这就是学习基础的差距,他们知识面、思维延展性强很多,所以我特别喜欢搜集他们的范文。”

图 | 摄图网
事实似乎证明,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学习效果。李志扬2006年在湖南长郡中学就读,也是尹飞上直播课时“屏幕另一端的学生”。在接触了一些从收看他们直播课的学校转入长郡的“尖子生”后,他发现出现负面效应的问题在于“下面配套措施做得很差”。
他向我们举例说,除了当地老师如何参与配合的问题,在长郡这样的“超级中学”,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心理辅导,也会有各种小组活动,同学们大都家境优良,基本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在整体心理建设方面要比底下的学校好很多。“因此大家不容易气馁,考差一次的没有关系,重头再来。”
因此,自己在做远程教育的上海微三公益创始人顾思毅总结道,“远程教室项目最麻烦的就是后期运营。”“大家都认为只要把大屏幕电视装上,把线拉上,然后课放上去,农村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只是最开始。”
作为教育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刘泓认为带来一些偏远地区学校改变有很多因素,直播课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其他更为重要的几个因素被此前的报道忽略了:一是政策性倾斜(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二是人(比如校长、老师、本地教育局)带来的改变。
他认为,随着专项政策的出台,很多相关学校会将学校资源倾斜到符合专项政策的学生,集中培养,然后带来了二本、一本、乃至清北学生人数的增加。“一两次的成功会带来边界效益(影响其他班)和良性循环(带来更好的生源)。”
为了能够从直播课中尽量受益,现在使用这种方式教学的学校会想很多办法,就像刘泓所说的,很多网课班的同学会受到“特殊待遇”。
来自成都某县级中学的纪晓玲告诉本刊,他们这两个上直播课的班被学校单独放了出来,和比他们高一级的班级在同一楼层,很少和同年级的同学有交集。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还得直播听网课,“其他班同学都在运动会,就我们两个班坐在教室中,特别心塞。”而这种“抱怨”又会引起另一场关于“教育公平”话题的争论。

“2006地球第三极珠峰大行动”的志愿者给西藏定日县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学习、娱乐用品,并在这里建立了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初中无线远程教育工作站。(图 | 视觉中国)
最终,人们会从考试结果论英雄,但直播只是因素之一。云南禄劝一中的同学成绩有了很大进步,纪晓玲说,他们班和另一个没用直播课的班成绩差不多;大凉山西昌一中的同学则说,上了直播课的班级还不如没上的……结论又回到了刘泓所说的那样,带来改变需要很多因素,仅靠直播课是不现实的。
但没人会否定学校间与学生间交流的意义。“总体来看,我觉得学生能接受很多新鲜东西,开阔视野,也对他们加宽加深知识面有好处。”四川梓潼中学的张老师这样总结道。在接入了成都七中的直播课之后,他虽然也在教学中遇到了上述种种问题,但也有很多收获。“比如我教英语,我就觉得成都七中的那个思维导图很有用,能开放学生的发散思维。”
相互接触得越多,相互之间总能碰撞些火花。李志杨告诉本刊,对于长郡中学来说,其实直播班的同学很容易比周围的同龄人要自信。“因为输出直播的班会收到很多底下学校寄给大家的信件。你可能在直播班上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同学,但是只要你在直播课上回答了某些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被直播远端的同学注意到,他们都会给你写信。”
“所有人都收到过。”李志杨补充说,而且“那些信都是充满着热情,充满着真诚,非常动人”。
为了促进这种交流,长郡中学每学期会组织一次实地交流活动,长郡的老师会带一些同学到屏幕那边的学校去。据李志杨回忆,去过的同学给出的反馈都还蛮积极的。“我觉得就是经常去一些学校,你会感受到善意,这对于促进整个教育是非常有益处的一个事情。因为人只有感受到他人的热情,有制度激励之外的东西,才能让大家在教育上做的更好。”
在屏幕另一端的尹飞尽管对直播课的评价不算积极,但他也能回忆起交流带来的快乐。“我高二的时候,长郡的老师有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很高兴、很开心,像群星簇拥一样,大家抢着和老师聊天、合影。”
高中毕业四年,纪晓玲回想起来,觉得直播课对她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目前在重庆上大学的她认为,直播班的教育开阔了她的视野,让她在进入大学后不至于会感到落后。“我们在县级地域很难看到一些‘未来’的东西,”她说道,“越是落后的地区,越强调学科知识上的内容,而成都七中的老师能帮助我们拓广知识面和视野,不局限在教材。”
必须要说,上面提到的邵东七中、西昌一中,和之前报道里的禄劝一中都是个例,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我们无法从几个例子出发就得出远程直播课是否应该推广或暂停的结论,这些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事实上,任何行动都强过坐而论道,而如何将行动的成果变得更广泛、更深刻,则是这波热潮带给我们的思考。

图 | 视觉中国
回到争议的起点,从科技与教育结合的角度出发,很多对此感兴趣的人会想起“每童一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计划。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发起并组织了这个计划,其宗旨即借由生产价格低廉的笔记本电脑,赠送给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孩子,令他们也能透过科技进行各种学习活动,消除知识鸿沟。
但这项看上去极佳的科技改变教育的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汶川地震时,“每童一电脑”项目曾给都江堰的一所学校免费送去了1000台电脑。可是,这些学校只用了一个月,就把电脑全部锁起来了。一是“每童一电脑”没有派人去当地指导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二是当地老师发现电脑中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毫无帮助。
在拉丁美洲,秘鲁政府5年来投资超过2亿美元在公立小学发展“每童一电脑”辅助教学计划,却因师资不良及其他配套不足,导致成效大打折扣。有机构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Jose Arguedas小学共有570名学生,该校透过政府推广分配到的40台低价笔记本电脑鲜有教师在课堂上使用。该校科技主任就无奈表示:“许多老师不知如何运用这些电脑。”这看起来与一些远程学校的老师在有了远程直播课后就撒手不管颇有相似之处。
秘鲁教育部官员马尔柯(SandroMarcone)则说:“简单来说,我们至今做的只是配发计算机,却没有培养师资。”调查报告的作者则表示:“外界起初幻想光靠科技就能带来改变并改善学习环境,但这项调查的结论并非如此。”
在《老派科技的逆袭(The Revengeof Analog)》这本书中,记者戴维·赛克斯(David Sax)采访了纽约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常务董事大卫·诺亚(David Noah),这所公立学校以其出色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闻名全美,被一些中文媒体戏称为“美国衡水中学”。在采访中,诺亚表达了一个观点,即“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或许与教育科技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改革涉及更多的是老师之间的合作、较长的学习天数、课前课后辅导计划的资金……这些都不是科技推动的改革,科技只是这些改革的次要部分。”
由此,作者戴维·赛克斯总结道:“‘每童一电脑’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假定了那些闪亮的高科技具有普适性,却不相信更了解眼前问题的人提出的建议。”而他给出的判断则是:“教育的创新之中,真正可以持续下去的不是各种硬件和软件,而是形塑学生学习的新教学法。”
回到国内的场景中,杨临风也有相似的观点,即:“中国教育的症结其实在于我们的教学方法出了问题,造成绝大多数孩子不爱学习,或者很想学却学不好。”他同时也呼吁,在云南禄劝第一中学的案例背后,在“屏幕改变命运”刷屏背后,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也是当地教育局、学校和老师们苦心经营的成果,绝非一句“科技改变教育”能轻易概括。
这也是过度强调技术带来的一个问题——弱化了远端老师的角色,他们成了配角。梓潼中学的张老师就向我们坦白说,他有时也会觉得自己仅仅是个维持秩序的人,似乎失去了老师应有的价值。而所有人都明白,没有老师在实地的指导和监督,哪有学生能独自完成学习的任务呢?
而一直做教育公益的刘泓则希望公众能借此思考一个价值观问题——高中教育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谁?“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过程才是教育真正该关注的地方。”
(文中的老师和学生均为化名)
大家都在看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未来学校:如何让孩子成为“未来之人”」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