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挚行者张守岳在沅陵县第一中学驻扎的第一个月认识了一位“咖啡姐姐”,了解了她作为一位听障人士,在成长、生活中遇到的不便。县域的残障议题相较于城市有何特殊性?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支持身边的残障人士?守岳的手记也许可以让你获得关注残障议题的共情基础。
作者丨张守岳
PEER空间项目部

残障议题在县城
据中国残联2018年统计,中国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超过一成有劳动能力、达到就业年龄却未能实现就业。尤其是在县镇,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中主动或被动的“消失”了。接下来要讲的咖啡姐姐的故事,或许对我们理解这一议题有启发。


在市场的残障人士,图源:Unsplash
“
咖啡姐姐的故事
咖啡姐姐在青少年时代与常人无异,在当地县城幸福地长大。然而,十八九岁时她的听力骤然下降,在教室里听不清老师的讲授,成绩一落千丈,按成绩排座位越排越靠后。可离讲台越远,她越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父母带她去看医生,可彼时的医生医术低劣,甚至没有测她的听力,误诊为注意力不集中导致成绩下降。
那时的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上了大专,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可每当老板呼唤她没有回应或者她反应慢半拍时,老板就以为她“脑子不好”,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了她。
回到家后,她结了婚,做了全职太太。她生了一位性格开朗的男孩,陪儿子长到四岁时,她受广州一家为听障人士提供岗位的咖啡馆的启发,毅然走出家门,投入了咖啡行业。她总共花了七年的光阴才从抑郁中走出来,接纳了这个现实,找到了自己擅长做的事。
她告诉我,县城里不是没有残障人士,只是他们不敢出门,才消失在人们视野中。从她的经历来看,父母、老师、医生、雇主都没有提供给她一个足够包容、支持的环境,她被迫待在家里,缺乏与外界交流,听力与心理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她原本计划以做一年咖啡作为她走出社会的第一步,以此接触服务行业,学会交流,磨炼性格,但是不知不觉做了快两年了:残障人士拓宽职业路径也更加艰难。
哪怕自己过得很辛苦,咖啡姐姐仍然一心想为残障孩子们做点事情。她连续七年每年去残疾学校看望孩子们,每年组织其他残障人士一起东拼西凑为孩子买需要的东西。虽然县城有定点帮扶企业每年给青少年特殊学校配发助听器,可她发现助听器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只,戴在一只耳朵上,而且助听器没有根据孩子听力损失情况做调试。如果孩子只单耳佩戴分贝不合适的助听器,反而会造成两耳听力水平畸形发展,起了反作用。精准扶贫需要细致地了解服务对象需求,不宜“给坐轮椅的送拐杖”等形式化的献爱心。
县镇的融合教育进展也不如大城市快,残障人士职业发展不够多元。融合教育指的是轻度残障的孩子进入普通学校与健康孩子一起学习、生活。而县镇的学校对于接收这类学生有很多顾虑,如果家长无力负担送孩子去大城市融合教育学校的费用或者没有这个意识,只能走上送盲童去盲校学按摩、将来做按摩师的老路。
而如果突破这一刻板印象,听障人士为什么不可以去幕后做咖啡、做面包呢?上海的“熊爪咖啡”就提供了一个有爱的范本,听障咖啡师在幕后做好咖啡,通过一个小洞用熊掌托着咖啡递给顾客。而长沙的“巴赫西点面包店”也特意聘用残障人士制作面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咖啡姐姐制作的咖啡
“
我的故事
作为同样有轻微听力问题的我,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我从小就被发现了有轻微的神经性耳聋,而我的父母一直不遗余力地为我治疗、定期测听力。虽然神经性耳聋是不治之症,但近些年每次测我的听力都在变好。在城市长大的我,获得了身边人的包容、尊重。我告诉自己,听弱与近视一样,戴助听器与满大街戴眼镜的人没有本质不同。
不了解情况的同龄人熟悉我后会发现我的“反射弧比较长”,即遇事回应会比较慢。而如果要与谁长期共事,我会一认识时就诚恳地请求对方以后对我说话大声一点。班主任会趁我不在教室的时候跟全班同学说明情况。我唯一一次被一个同学嘲笑后,听闻消息的班主任立刻冲来教室把那个同学叫了出去训了一顿,我仍记得老师对此义愤填膺地回应“这是品德问题”!我高考英语听力考试需要戴助听器进场,老爸跑了多个单位获批同意给予合理便利,监考官知道后对我一切照常,完全没有打扰到我的考试。
我在去美国读大学时,学校残障办公室的支持力度更大,只要你写申请,他们就会通知授课教授提供便利,只告知教授他们需要怎么配合,并不说病因,最大程度保护了学生的隐私。学校还提供小巴每天专门接送行动不便的同学上放学。走上职场后,美国人如果被老板因残障而解雇,必将老板告到损失惨重。他们使用的称呼也保障了“残障人士”(people with disabilities,PWD)的尊严,而不称呼其为“残疾人”(disabled people)。我学英语时就以姚明为榜样,他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当他在NBA名人堂入选仪式上轻松自如地讲美式笑话时,便激励到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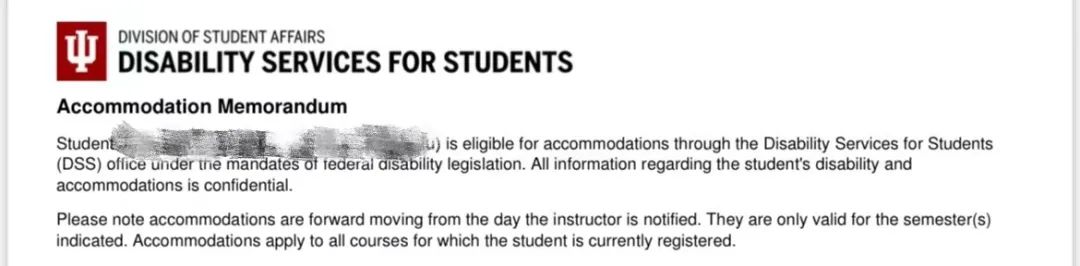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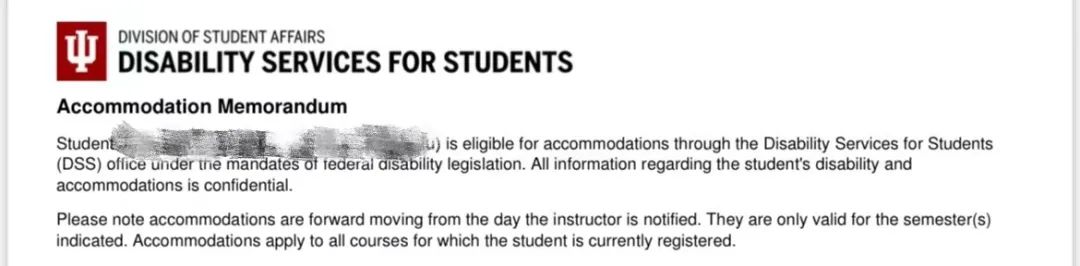
一所美国大学残障办公室通知教授为残障学生提供便利
“
对比与反思
对比咖啡姐姐和我的经历,能感受到对残障人士的关怀上存在的国际、城乡和阶层差异。
如果咖啡姐姐身边的人也能像我身边的人那样支持她、保护她的权利,她就不会有那么坎坷的人生经历。咖啡姐姐认为我的经历也启发到了她:如果一位残障人士综合能力足够强大,就能强到完全可以让周边的人忽略他的残缺。为什么这个小缺点一度带给她带来很多困惑,其实就是那时不够强大和饱满。
似乎身为残障人士很难改变落后于自身需求的帮扶政策,但是这一切都有在慢慢变好。她说,“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社会的包容也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地融合进去;各类行业也需要我们自强,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各种平等需要我们用自身的能力去说话,看到你我更加明白和确定这一点。”
我在做2019年PEER暑期项目线上培训导师时,当仁不让地选择了带“残障与融合”议题包小组。这个议题包关注县镇残障人士的融合教育、就业,当地人对此的看法与基层机关对他们的服务等。在听咖啡姐姐的经历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县城的残障问题有何特殊性,而现在我意识到改变那里的制度性歧视、提升全社会的无障碍服务意识,任重道远。她和我愿意站出来,鼓励更多特殊人士发声,让更优秀的特殊人士被看见,使残障与融合政策更加精准对接需求。作为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其他病友,PWD HELP PWD!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它怎么对待弱势群体。如果你有余力,请捐款支持帮助残障人士的公益组织及福利机构,或去那里做义工;哪怕人微言轻,也请你在街上遇到他们时予以尊重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回忆冬残奥会盛况,请为残奥健儿喝彩,传播他们自强不息的故事。
希望未来有一天:每位县城的残障儿童家长都不必把孩子送到大城市,就能根据孩子的病情送到家门口的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或特殊学校培养多元技能;每位残障劳动力都能壮有所用、老有所养,自信地走在大街上。


想读守岳的更多个人日志?
欢迎关注左侧公众号
ID:“桃与棘”



关于PEER毅恒挚友
PEER毅恒挚友是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并发展博雅、人文与素质教育的非营利组织。
截至2021年9月,PEER 在湖南、贵州、陕西、甘肃、广西、湖北和吉林的30所初高中累计逾124次服务-学习寒暑期项目和专题项目,短期项目直接服务学生约8000人,参与项目志愿者逾1500人。
自2015年起,PEER 在湖南、广西、贵州的11所中学设立了自主设计的“PEER空间”,围绕中学生成长提供长期支持。每个空间驻扎1-2位长期志愿者,和中学生共同营造学习空间、生活空间和公共空间。







